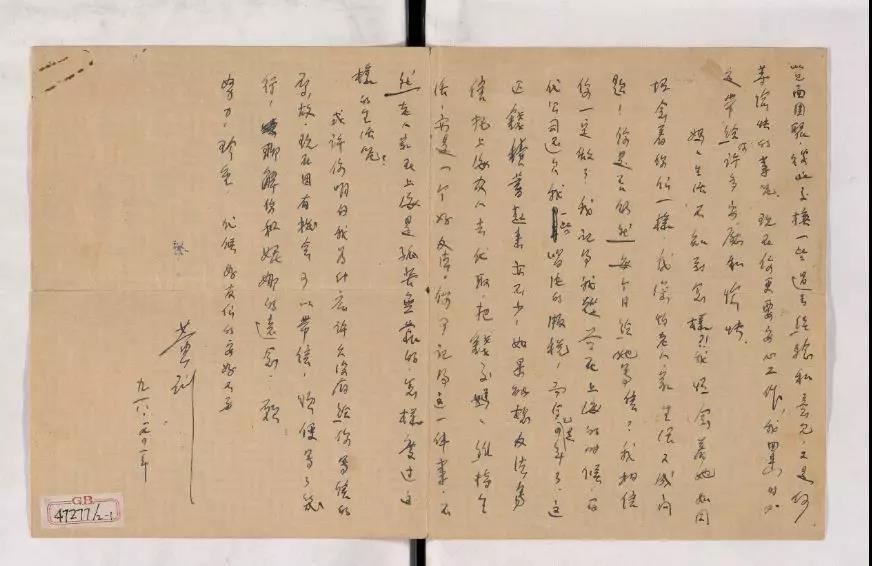文物保护看基层 | 一位文物修复师与千手观音的故事
| 2020-12-17 09:13:35来源: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责任编辑:陈静我来说两句 |
分享到:
|
|
当一个人用8年时间只做了一件事,可能支撑她的不仅仅是热爱,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大足石刻研究院保护工程中心主任、研究馆员陈卉丽就是这样一个人。12月10日,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跟随国家文物局组织的“文物保护看基层”(重庆)主题宣传活动,在大足石刻见到了她。 与记者想象的不一样,陈卉丽个子不高,带着眼镜,说话非常有条理,一讲起千手观音,她就滔滔不绝,充满激情。 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开凿于南宋年间,造像雕刻于15-30米高的崖壁上,有830只手,是中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集雕塑、彩绘、贴金于一体的摩崖石刻造像,是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的核心部分。然而历经800多年风雨后,千手观音造像受人力、环境、气候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早已病害缠身。陈卉丽带着她的团队,用了8年时间,最终将千手观音修复完成。 从“纺织女”到“文物工作者” 记者:你是如何开始从事文物修复工作的? 陈卉丽 :我原本从事的是纺织工作,和爱人结婚后分居两地,1995年初,在组织的关怀下,我从老家四川调到爱人所在单位—大足石刻博物馆(现大足石刻研究院)工作。很快,有材料分析、化学学科背景的我,被分配到保护工程中心工作。 当我第一次近距离看见那些不会说话的石菩萨时,我就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这也许就是我和他们的缘分吧;也许是因为个性要强,我绝不容许自己对工作哪怕有一点点的不负责任;也许是每一天都望着悬崖峭壁上那尊尊精美绝伦的菩萨造像历经千年风雨侵蚀,慈悲虽在、容颜却改,触动了一个女人内心深处的柔情,我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这些不会说话的石菩萨,从此也就与文物保护修复结下了不解之缘。 因为担当,所以要创新 记者:从事文物保护修复工作有什么特点? 陈卉丽:文物价值的多样性以及文物的唯一性,决定了文物保护需要科学的保护修复理论、原则及方法,并在其指导下进行科学的保护修复。同时还要根据文物属性特点不断探索文物保护、艺术效果、公众需求之间的平衡。 此外,文物保护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病害研究、保护修复工艺及操作、材料及设备、环境分析与控制、档案建设、美学讨论等内容的系统工作,是一个由考古、艺术、物理、化学、材料、生物、环境、地质等多学科分工与合作的过程。需要多学科交叉融合支撑文物保护工作。 而且,保护工程实施秉承“思与行”的工作思路,采取”多学科联合攻关”以及传统的工程手段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文物保护项目,使文物病害得到有效遏制,确保文物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记者:在修复千手观音的时候遇到过什么困难?如何克服的? 陈卉丽:修复文物不是想当然的修饰。在修复中必须坚守文物真实性第一的原则;就像断臂维纳斯一样,在没有准确依据的情况下,是不允许擅自“创新”的,否则就是对文物历史真实性的破坏。正因为这样苛刻的要求,让文物修复工作每一步都充斥着更大的困难和挑战。 在对千手观音石质胎体残缺部位进行修复补形时,要根据史料、造型本身的对称性,辨别出残缺手部原本的模样,再对缺失部位延伸补形。如果找不到依据,只能保持原样,也不能擅自发挥。 但是在修复千手观音的主尊像时却遇到了新的难题,我们发现主尊右边前伸的主手自腕部残缺,现存手掌及布帕为后人补塑。后人补塑的手帕造型不仅改变文物历史真实性,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造像的美观性。 为修复这只手,我和同事一起反复考察研究千手观音手型,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以及佛教经典,也没找到修复的依据;于是我带领同事先后对四川、重庆、河北、山东地区等三十多座石窟的观音像进行实地考察,试图找到其修复依据,很遗憾最终也没找到可靠的依据。此时,我觉得花了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都是徒劳的,真的好像是山穷水尽疑无路了,并且感觉身心疲惫,对修复这只手已经没有信心,决定放弃这只手的补形修复,让我们的后人找到科学依据后再实施修复…… 虽然自己有放弃修复这只手的想法,但是在我心里始终牵挂着这只手的修复工作,这事也让我夜不能寐。就在这时,我想到了郭相颖先生、詹长法先生他们退休后还一直关注文物保护工作的这种退而不休的敬业精神,我不能因为遇到困难就轻言放弃的;这次修复是千手观音造像800多年来第一次最全面、系统、科学的修复,如果这次我们不能修复好这只手,就会留下终身的遗憾;同时也对不起关心我们文物保护工作者的社会各界,因为大家都想看到修复后完整的千手观音造像…… 为此,我和同事们又夙兴夜寐地研究、讨论,评估修复的各种利弊。修还是不修?成为一个难题也牵动着大家的心。修,就会违背真实性原则;不修,又会极大地影响造像的完整性。最终,我在基于对文物修复的真实性要求,并对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综合考虑的基础上提出:依据千手观音造像对称原则,按照另一侧相对应手的形态,采用“可拆卸式的”修复方法来修复此手,以便于后期再次修复处理,我的这一创新思路得到了文物专家的一致认可。于是按照另一侧相对应手的形态,给千手观音装上了一只可以拆卸的手,在保证造像艺术完整性的同时也为后人修复留下了空间。 因为爱而担当 记者:能否讲述一下工作中最难忘的一两件事。 陈卉丽:2008年5月,国家文物局将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修复列为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而那时,千手观音造像病害已达34种,拯救“千手观音”刻不容缓。 我清楚地记得,2008年6月12日上午,当领导安排我作为大足石刻研究院现场技术负责人带领团队参与“一号工程”时,我心里很是激动,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说实话,很多老一辈的文物保护专家做了一辈子的文物保护工作,也没能遇上像大足千手观音修复这样如此具有挑战性的保护项目,我能参加这个国家一号工程的修复,真是非常幸运。同时又感到压力巨大,因为工程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在世界上迄今为止尚无可参考的案例,修复过程中出现的每一个问题,都将是世界级的难题。而且,让我更没想到的是,项目总负责人、原中国文化遗产院副院长詹长法研究员提议我担任石质修复组组长,这意味着我们团队将承担起修复工程中最重要的石质本体修复任务,这种巨大的压力和由衷的信任令我终生难忘。 修复千手观音这类大型不可移动的露天文物,作为修复人员在身体和技术上都会遇到很多困难。在石刻修复现场狭小的空间里,修复人员每天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长期嗅着刺鼻的材料味、粘得一身尘土,或站、或蹲、或躺,一个姿势就是一整天,就像手术台上拯救病患的医生,不敢有半点疏忽,因为文物的生命只有一次!加之文物保护环境的限制,再热不能吹空调,再冷不能用烤炉,我们不得不克服冻疮、蚊虫叮咬、化学试剂过敏等身体上的折磨。由于修复工作的特殊性,需要长时间固定一种姿势,所以颈椎病和腰椎病也不可避免。 记得2011年6月的那个夏天,比记忆中的任何一个夏天都要更加闷热。按照工程进度安排,那段时间,我们必须开展修复材料的大漆实验。可是不久我们就发现,因为长期接触大漆材料,加上天气闷热,大部分工作人员的皮肤开始出现大块大块的红疹,甚至开始慢慢溃烂。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没有一个同志主动请假、要求休息,全都不声不响,硬是整整熬过了那个不一样的夏天。 我还记得,团队中的彭柳升同志,老家湖南,2012年母亲患病去世,因为坚守工作岗位,没有送上老人家最后一程,至今还在心里留下了对母亲的无限愧疚…… 团队中的张俊杰、苏东黎、李元涛、韩秀兰、冯太彬等同志,每一个人都有讲不完的故事。 2015年6月13日,对于我和团队来说,是一生永远难以忘记的一天。当我们看到千手观音“金光再现”的一霎那,心潮澎湃、思绪万千,眼泪不自觉地顺着脸颊悄悄淌落下来,8年多来的修复工作历历在目:15家参与单位,100多名工作人员度过了3200多个日夜。 记者:你怎么理解文物修复工作? 陈卉丽:文物修复就是一种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这种精神倾注的是时间、是精力,更是情感和责任,而展示给我们的就是一段段鲜活的历史画卷。而我自己更深深知道,保护文物,就是守护我们民族和国家过去的辉煌,今天的资源,未来的希望。 做文物修复,除了专业技能,还需要有超强的耐心、高度的责任心和坚强的毅力。 在跟文物打交道的漫长时光里,我与它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在我心中,它们不是冷冰冰的石头,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个成功的文物修复师是可以和它们交朋友,用内心与它们对话的。每当和它们对视时,都仿佛听见它们在一一倾诉病情。文物修复师用专注和热情为它们祛除病痛,恢复健康,让它们延年益寿。 对自己来说,只有修复文物,才能让我内心真正平静,我愿为此坚守一生。 由于长期身处狭小空间,长时间固定保持一种姿势,大多患上了不同程度的颈椎病或腰椎病。可能大家还不知道,其实我们还患上一种更严重的“职业病”,那就是无论走到哪里,只要看见文物,我们就会不由自主地盯着文物看,看有没有什么病害,如果有,又该要用什么方法来为它们治病,让它们恢复健康,延年益寿,在别人看来我们似乎有点“神经质”,其实这是我们对文物的热爱和责任使然下而自然流露出的一种职业本能。 我也希望能有更多“守得住寂寞,练得好功夫,有责任敢担当”的年轻人加入我们的行业,才能让文物有限的生命得到更好的延续。(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 成琪) |
相关阅读: